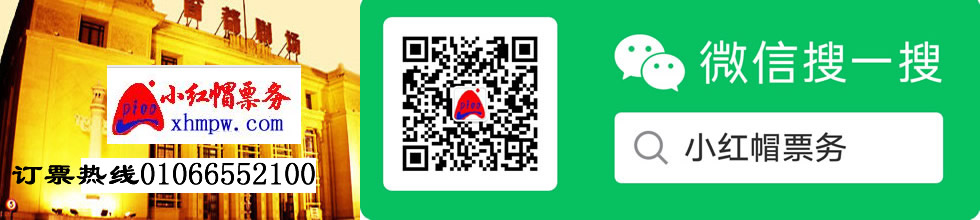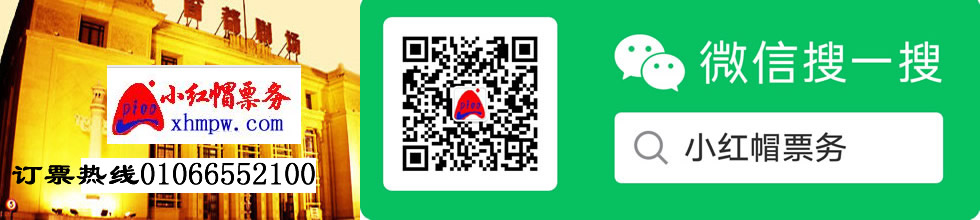|
在现实主义的话剧创作里,道具就像一个个无言的角色参与其中,而它们背后,道具师就是良匠,是大管家,是用巧思与应变为舞台效果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。
·博物馆里的话剧史·
“要讲究,不要将就”(节选)
刘琳
1958年仲夏某日,阳光明媚。“而无车马喧”的北京朝阳门外大街上,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,只见一匹健硕漂亮的棕红色马由西向东飞奔而来。不一会儿,又有几位身着古代战袍的士兵策马扬鞭从远处追来,正在执勤的交警和眼尖的看客瞥见他们全副武装、妆容浓重,紧随前边那匹脱缰之马绝尘而去。路人纷纷驻足观望,有人以为是电影街拍,可找了半天也没看到摄影机位,恍然以为自己进入梦境,来到了七百年前的元大都……
这一年,元代剧作家关汉卿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定为“世界文化名人”。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创作七百周年,六十岁的田汉创作了《关汉卿》一剧,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,导演是焦菊隐和欧阳山尊。第一幕的场景是元大都街市上,关汉卿目睹被诬陷的少女朱小兰行刑前的情景。毛驴拉着朱小兰的囚车上场前,监斩官和骑着高头大马的卫兵先登台招摇过市,表现出元朝官吏的淫威,关汉卿看到此景义愤填膺,后来才写出感天动地的《窦娥冤》。在舞美处理上,欧阳山尊做了很多大胆的突破,其中之一就是让真马真驴上台,并且不是仅仅走一个过场,而要在台上稍事定格,起到衬托剧情发展、营造场景真实感和加强视觉冲击力的作用。于是,找到这些“活道具”便成为该剧道具师丁里的重要任务。
学生时代,丁里就是活跃的戏剧爱好者,他所在的“七七剧社”和蓝天野、苏民所在的“祖国剧团”曾共同演出。当时条件艰苦,没有像样的剧场,每演出一个剧目,学生们要兼任各种工作,从布置舞台到卖票都得操心,正是这种经历锻炼出丁里开动脑筋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的能力。
这一次,丁里辗转找到北京军区通州双桥军马场,几经努力,借来六匹高大俊美的军马,五匹上台,一匹备用,连同日常朝夕相处、熟悉它们秉性的战士们。据说这些马原本是准备送到天安门国旗队“服役”的,进驻人艺后,就拴在自行车棚改造成的马厩里,战士们则住在剧场楼上。当时的首都剧场四楼(即现在戏剧博物馆所在地)是职工宿舍,于是之等很多人都住在那儿。那段时间大家都给丁里提意见,说老丁你这不像话呀,夜里马就在那儿挠墙,吵得我们没法睡觉啊。丁里只好找来黄泥,把地和墙都垫厚,让马的动静小一点。
拉囚车的驴怎么办呢?丁里灵机一动,想起距首都剧场不远的灯市东口拐角有个冰局子——专门卖冰的冰窖。那时候大家都用天然冰,冰局子有个杨老头,每天拉着驴车到各处送冰。杨老头生活困难,答应送完冰带着驴来参加演出,只要求带着孙子一起来,管顿晚饭。开演前,饰演朱帘秀的舒绣文要在后台练一遍《蝶双飞》唱段,刚唱两句,拴在院里篮球场的驴也应和了几声,饰演朱小兰的李滨心里嘀咕,驴到时别真在台上唱起来。幸好这驴还算聪明,每天开演后都听从杨老头的口令,准确地将车拉到台口,定格,配合李滨演完“朱小兰和前来祭酒的婆母无言啜泣”这场戏,从未亮嗓。可还是有一天,正赶上日场演出,眼见就要开幕了,驴还没来,原来是杨老头上西城送冰去了,丁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,演出时只好安排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李滨上台了。
1958年6月28日是北京人艺《关汉卿》首演。这一天,国内至少有一百种不同的戏剧形式、一千五百个职业剧团,同时上演关汉卿的剧本。想来是台下那匹备用马感受到了当天热烈的氛围,看着同伴风光登台实在心有不甘,于是在同伴们完成演出下台的一刹那,它毅然挣脱了绳索,不须扬鞭自奋蹄,挺胸抬头地飞奔出去!刚下台的战士来不及卸妆,骑着马直接追出去,才上演了这出“穿越大剧”。幸而当时路上没有私家车,战士们终于在某个路口追上了它,慌忙之间,有一名战士还付出了骨折的代价。
活物上台,无形中给舞台演出增添了生气,也达到了导演想要呈现的特殊艺术效果。在曹禺的名作《北京人》中,有一只久入樊笼的鸽子,从鸽笼中放出来时,它已不会振翅高飞,表达了丰富而悲怆的意味。为此,剧组特意买来几只鸽子,每晚演出前,负责道具的年轻同事用胶布将鸽子的大翅缠起来,为了不伤害到它,总是轻手轻脚。鸽子似乎也明白自己的使命,很安静地配合着。等到演出结束,道具师再解下缠绕的胶带。剧中的三幕二场,鸽子在舞台上踱步,道具师孙鋆毅就在上场口的侧幕条紧张地盯着,万一鸽子飞到观众席,他就要第一时间把它逮回来。与此同时,在下场口也安排了一个人,鸽子若自己走到了下场口,得让它赶紧归笼。 
洪吉昆制作,纸制仿唐三彩马
一
在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里,还有另外一匹马,同样剽悍健壮,挺拔昂扬。在舞美厅的展柜中,它悄然静立,通体白、赭、绿三彩的经典釉色,满带盛唐特有的绚丽,闪耀着不易被岁月剥蚀的光泽。1954年,北京人艺上演曹禺新作《明朗的天》,在布置剧中的豪华客厅时,道具师匠心手作,让这匹仿唐三彩马高踞于欧式的壁炉上,西式的房间立刻有了厚重的中国味道。
有一位道具师傅叫洪吉昆,原来是做楼库的。“楼库”这个词对现在的人来说很陌生了,简单地说就是做出殡时,烧给逝者的纸人纸马、纸扎的房子这些烧活儿的。洪师傅到了剧院后,最拿手的就是用草纸板做一个坯子,不管是茶壶水碗,还是古董水缸,在坯子的基础上再用纸浆或者其他材料堆砌成型,然后在外面刷上特制的轻粉(用骨胶和滑石粉熬制而成),再上颜色,晾干。人艺的戏剧博物馆现在还保留着一件他做的唐三彩,极其逼真。这样的道具重量轻,方便换景,不怕磕碰。
——蓝天野口述《北京人艺舞美往事》
而今,每当讲解员提示这是一个纸制道具时,人们无不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,凑近去观看它的每一个细节,可那硬朗的造型、浑然的做工,一点看不出纸制的痕迹。在它的旁边,还有几件器型不一、形神毕肖的用具,从中式的烧水铝壶、装饰瓷罐到古希腊的陶制水具,无一不由草板纸制成。
1953年,北京人艺演出了建院后第一部大戏《春华秋实》,这是老舍为了配合“五反”运动创作的三幕话剧。剧院初排大戏,制作人员稀缺,便临时请来有近二十年裱糊经验的洪吉昆和他的师兄弟们来做道具。《春华秋实》的剧情从荣昌铁工厂为农村抗旱备荒生产大水车展开,舞台上需要放置一架齿轮状的水车,如果用真的,那得两三个人才能搬到台上,换景会很不方便。洪吉昆就用粗糙的草纸板做了一个中空的大水车,直径一米多,一个手指头就能把它挑起来,令舞美设计辛纯、韩西宇赞叹不已。洪吉昆说,不光这个,什么都能做,只要有真的,我就能用纸做成假的。两位舞美设计问他愿意到剧院来参加革命工作吗,洪吉昆激动不已,连忙说,愿意!只要够家里生活就行。这之前他光靠裱糊手艺已经难以养活全家,早就像祥子一样靠蹬三轮谋生了。自此,他绝处逢生,同时也成了北京人艺纸制道具的开山鼻祖。
北京人艺建院之初,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,虽然国家对剧院有补贴,但各项费用均要量入为出,当年一个大戏的制作经费有三千元就算十分可观了。为了厉行节约,舞美制作推崇的观念是“以假代真”,用真材实料不算真本领,用代用材料做出合乎演出要求、达到艺术效果的服装、道具,才算真功夫。
就这样,洪师傅精湛的手艺在1954年排演的几部大戏中都有展现。在《明朗的天》那匹唐三彩马之前,还有一匹马。上演苏联戏《非这样生活不可》时,剧组从大使馆借来一座铜马,分量很重,一个人搬怕摔了,两个人搬怕碰了,好在有洪师傅,做个假的吧!他就用纸在铜马的表面盔了个模子,按传统手法揭模子要先用刀切开口子,这很容易划坏铜马的表面,洪师傅想起自己少时在艺徒学校学习的钣金锻冶技术,便用细铁丝沿着铜马的轮廓糊在模子最内层的纸里,留出引子,待模子全部盔好后,揪住铁丝引子一扭,模子很容易地就揭下来了,然后再按马的外形琢磨细部,上色上油。
《明朗的天》中某位医生的家里有个铜盘茶几,负责采买的人到商店一看,好家伙,得花五十块。洪师傅说,咱不花这钱,自己做。先由装置组的木工做框架,三合板做出台面,然后由洪师傅做装饰,纸砌边缘,纸雕龙头,只用三天工夫,四个龙头叼着一个铜盘的茶几交活了。这纸木结合的新尝试,既省工省料,又轻便耐用,为道具制作开拓了一条路。后来《雷雨》中百分之八十的家具都是道具组制作的,比如周家客厅中那套侍萍年轻时喜爱的硬木家具,也是用纸木结合的方法打造的,洪师傅通过剪、拉、画、烫、雕花刻纹等手法做好,然后上色着漆,那些样式繁复的浮雕便被一一复刻在灯光幽暗的周家客厅里,圆桌、百宝阁、衣柜古色古香,沉稳厚重,彰显了周朴园民族资本家的身份。沉浸在演员表演和戏剧冲突中的观众可能很少会想到,这满台的装饰布置蕴含着多少制作人员的匠心和汗水。
洪吉昆将纸扎技术带入北京人艺后,边英凯也被吸收进入道具组,他多才多艺,能写能画。经过潜心钻研,他将纸扎技术进一步精细化、艺术化,在制作工艺和材料上不断尝试探索,发展出能够满足多种道具需求的制作方法。比如在材料上,他将泡沫塑料通过热力丝拉出各种花纹,不但可以做青铜鼎上的浮雕纹饰,还可以制作外国戏中的洛可可式建筑。再比如沥粉技术,他将滑石粉和骨胶混合在一起,像蛋糕裱花一样,挤出各式各样的图案,立体感很强。还有戏中那些永不凋谢的花朵,有时是用绸缎做的,更多还是纸制的。 
《蔡文姬》道具,纸制仿青铜酒具
随着剧院创作题材的多样化,道具制作的创新能力也被锻炼和激发出来。1959年国庆,北京人艺演出了八台献礼剧目,包括《雷雨》《带枪的人》《伊索》《蔡文姬》《悭吝人》《日出》《骆驼祥子》《烈火红心》,涵盖了古今中外各类题材,加上未列其中的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,足以宣告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形成。细细盘点其中的每一部戏,舞美制作人员的创造和贡献无处不在,并且剧中的很多道具一直沿用至今。
2020年北京人艺六十八周年院庆前后,蓝天野先生在微信朋友圈“即兴以图文忆往”,不定期分享九宫格,追忆往昔岁月中令他不能忘却的合作伙伴。六月的一天,他发了一组不甚清晰的老照片,大部分是泛黄或翻拍的黑白照片,配文写道:
激动一天,泪流满面!
早想写北京人艺辉煌时期的舞美制作工厂,那可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棒的!可惜,缺少资料,无法落笔!
今天,几位热心人提供了珍贵资料,这资料的获得详情,就先不说了。
服装:(中装)姜文山师傅,(西装)谢宗荫师傅,(中装)刘邦声师傅。
道具:洪吉昆师傅。
化装:李俊卿师傅(大李)。
效果:冯钦。
装置(制景木工):杨金良师傅,梁国栋师傅,张宗林师傅……(暂不全)。
现在也先不说哪个图是哪位了,顾不上,马上发!
照片中的面庞是那样朴实无华,在每部戏被搬演上台的过程中,他们是一个默默无闻但不可或缺的群体。经过他们的巧手,那些设计图纸上的形象变为现实。在北京人艺对舞台“完美整体感”的孜孜以求下,他们的技艺经过不断的打磨、创新和幻化,成为舞台整体形象的一部分。旧日时光渐行渐远,这些前辈的名字和样貌已少有人识,但他们的技艺和匠心手作却代代传承。 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北京人艺道具组工作照(中为丁里)
二
我为什么搞道具呢?是有原因的。在《民主青年进行曲》里,我演一个工友。有这么一场戏,一个学生拿着一沓纸币,那时候叫法币,扔一地。我要捡。我这个演员糟糕在哪呢?高度近视眼,又有散光,工友这个角色也不能戴眼镜。灯光一打,基本就是一个瞎子了,看不见,捡这钱可是大问题了。因为你得很短的时间把这钱都捡起来,而且那个演员撒的时候没有规律,一撒一片。如果是楼上的观众看台面一目了然,落下一张都不行。这是个大难题,因为我不捡的话不合剧情,捡的话时间太长,观众就甭看别的了。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,女同志戴的那个项链还有老和尚戴的素珠不都是串起来的吗?我就利用这个原理,把票子用一根黑丝线——当时还没有尼龙线,就是很细的黑丝线,扎上眼儿串起来,这学生一扔就散开了。观众不知道有根线在那儿串着呢,只要我看到票子,拿到一张,做那种假动作,一下就拿起来了。这是根据我的角色,根据剧情来搞的,要不然这事不好办。后来领导一看,反正你这眼睛也甭当演员了,就干这个吧。这一干就干了一辈子。
——丁里口述,摘自《岁月谈往录》
人称“丁道长”的丁里从北京人艺建院起就是道具组组长,群众发挥智慧给他起了这个一语双关的名字,有时干脆就叫他“丁道”。其实丁里本名叫曹用礼,北平解放前夕,他也成为众多投奔石家庄解放区的热血青年之一。他和同学李守海结伴而行,为了安全,当务之急还是那道必答题——先改名。他俩拿起一张《晋察冀日报》,决定指字为名。李守海随手一指,竟指了个“肉”字,叫“李肉”?着实不雅。曹用礼开玩笑说,你干脆叫“李肉丁”得了!李守海说,那就把“肉”去了,叫李丁吧。曹用礼也懒得再想了,你叫李丁,那我就叫丁里吧!
建院之初,剧院没有家底,每排演一部新戏,道具人员就要想尽各种办法备齐道具。丁里脑子活,记忆力好,出于职业习惯,平常每到一处,待上五分钟,他就把房间里的家具布局、大小摆设尽收眼底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这叫照相机式的‘缩微式头脑’,除了抽屉里的存折我看不见,其他我都能给你说出来。”比如那时到财政部去演出,他就瞎溜达,看到人家会议室带扶手的椅子,就记下来,等排戏需要时,他就从记忆储备中调出这件东西。当时这种可以通用的道具以借为主,单位开个介绍信,公对公,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借了。他更为熟悉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、中国青艺等同行单位的道具库,像《骆驼祥子》里的洋车就是找中国儿艺借的,大家互通有无。
经过实践中的摸索,道具组人员的分工合作渐渐明晰。精于手作的洪师傅、边英凯负责制作,擅于沟通和变通的丁里负责管理和跟演出,俗称“跟戏”。跟戏极其考验道具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,无论是日常演出中的小细节,还是需要随机应变的偶发情况,在丁里那里都成为充满乐趣的机巧和历险。
人艺建院之前,丁里参与某部戏的道具工作。金雅琴饰演一位时髦女郎,要穿美国的“玻璃丝袜”,当时即便找得到丝袜也买不起。丁里开动脑筋,他让化妆师先在金雅琴腿上涂一层接近丝袜的颜色,然后找剧院装置组的木工借来他们的木工弹线,用黑油彩“啪”地在金雅琴腿肚子上弹出一条笔直的黑线,就像是丝袜的接缝。这装扮上了舞台足以乱真,天衣无缝。
《骆驼祥子》的开幕是在刘四爷的“人和车厂”,按照剧情,那是1926年冬天。刘四爷上场的时候是听书遛鸟回来,他手拿一把扇子,提溜着鸟笼子,手里头还有一对铁球。可大冬天谁拿俩铁球呀,多凉呀!丁里就把它们换成一对核桃,如果是夏天再用铁球。导演并没有提要求,丁里就直接跟饰演刘四爷的英若诚沟通。这些细节帮助演员确定了人物与所处环境的关系,建立起信念与真实感。
《雷雨》第一幕的尾声,周朴园累了,往沙发上一坐,拿起茶几上的吕宋烟要抽。茶几上的烟具里有一个搁火柴的盒,大少爷周萍拿起火柴一划,着了,他给父亲点上烟,周朴园吸了一口,吐出烟雾,闭幕。丁里的任务就是确保这根火柴一划就着。他将两根火柴并到一起,最初是用白线缠上,后来就直接拿胶粘上,这比一根火柴的保险系数高。如果一下划不着,不但破坏了场上的氛围和周朴园的威严感,也让饰演周萍的演员尴尬,很可能打乱整场演出的节奏。看似很小的细节,却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,可见道具人员责任重大。
1980年9月,《茶馆》作为中国话剧走出国门的首部剧目,赴欧洲三国演出。巡演是对剧院各岗位工作人员综合能力的巨大考验,特别是剧中的布景、道具要提前两个月经海运运送到演出地。在道具的准备工作中,丁里又发挥了智慧,比如剧中那些茶壶茶碗,当年大部分用的是纸制的。剧中李源饰演的二德子上场时,要顺手摔一只茶碗。丁里便准备了一些碎碗碴,每天开幕前把它们放在纸茶碗中,当二德子愤怒一摔时,碎碴溅落满地,保证了应有的演出效果。饰演王掌柜的于是之也没想到这一着儿,直到某天无意中问起李源,他才恍然大悟。
当年因为《关汉卿》中那头误场的驴,丁里写了检讨,这算演出事故。在那之前,他还经受过猫的考验。苏联名剧《带枪的人》场面宏伟,布景高大繁难,服装道具更是品种多、数量大。剧中有个角色每天要抱着一只猫上台,这只猫还要化装,带一个大红的领结。有一天快开幕了,猫却不见了,丁里忙问谁家有猫,一个同事把自己家的猫抱来了。丁里赶紧给它化好装,这只猫就上场了,结果它惊魂未定,灯光一打,一下就把演员用棉花做的假下巴给抓下来了!演员也不知道换了新猫,还纳闷,平常没这动作呀?情急之下,只好拿随身带着的手绢把下巴遮住,坚持演完了那场戏。一直到快散戏时,大家才发现那只找不见的猫,它正在台上一辆道具火车底下酣然大睡呢。 |